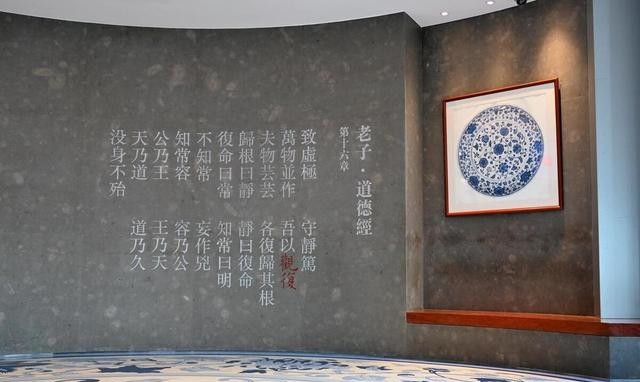从东南亚动身|兰纳国残影:清迈的梵宇与佛塔
泰国清迈是前史上兰纳国(Lan Na, 意为“百万稻田”,1292年-1902年)的政治中心,也是泰国北部区域传统上的释教中心。中文史料称这个政权为“八百媳妇国”,由于传说该国的控制者有八百个妻子,但其实当地人并不运用这个称号,“八百媳妇国”之名仅见于中文史料。在这个总人口不到30万的小城中现在仍有大约300座寺庙,可以说寺庙是清迈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现在看到的清迈规划较大的梵宇根本都与兰纳国的前史有关,包含清曼寺(Wat Chiang Man)、帕兴寺(Wat Pra Singh,意为“圣狮寺”)、松德寺(Wat Suan Dok,意为“花园寺”)、素贴寺(Wat Phra That Doi Suthep,意为“素贴山之寺”)、柴迪隆寺(Wat Chedi Luang, 意为“大塔寺”)、柴尤寺(Wat Jet Yot,意为“七塔刹寺”)和罗摩利寺(Wat Lok Moli,意为“至尊界寺”)等。清迈的梵宇和佛塔大约是旧日兰纳国留存下来的最首要遗址。本文以这几所典型的清迈梵宇为要点,简略介绍清迈梵宇的建筑特色以及其间包含的前史文明信息。由于佛塔(泰语称Chedi)在清迈的梵宇中比较重要,所以本文题目中特意以“佛塔”和“梵宇”并称。
清迈旧城区地图(显现部分寺庙方位)清迈梵宇的空间布局与建筑特征与北传释教寺院常见的递进式多重院子不同,清迈释教寺院大都只要一个围墙合围起来的大院子,大殿和佛塔往往占有梵宇的中心,其他建筑则依据状况安顿。这种以佛塔为中心的方形院子布局结构在柬埔寨吴哥窟也可以看到,表现了婆罗门教(前期印度教)的国际观。依据婆罗门教的国际观,国际的中心是须弥山(Sumeru),外围是四大部洲、大海以及铁围山。这种国际观也被后来的大乘释教和南传上座部释教承继,而佛塔就成了须弥山的标志。早在南传上座部释教(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的斯里兰卡)盛行之前,中南半岛有很深的婆罗门教和大乘释教传统,因而清迈梵宇的这种空间布局实践上也表现了婆罗门教对南传释教的影响。
左为我国杭州灵隐寺平面布局图,来源于网络;右为柬埔寨吴哥窟平面布局图,来源于网络
左为帕兴寺平面布局图,来源于网络;右为柴迪隆寺平面布局图,来源于网络清迈梵宇的正门和大殿一般都朝东,一种解说是这个朝向与太阳崇拜有关,此说当然有道理。一同也或许是为了朝向城东的宾河(Maenam Ping,又译“屏河”)。清迈区域一向以稻作农业为主,水源是整个社会十分名贵的资源,水也是南传释教典礼中十分重要的圣物。并且河流也是古代清迈区域首要的交通线,信众往往搭船到梵宇礼佛,因而梵宇朝着河流开门也最为便利。清迈城的正门塔佩门朝东,也是为了朝向宾河。同属南传释教的老挝万象区域的梵宇也往往朝着湄公河的方向开门(如西萨格寺)。但总体上南传释教区域的梵宇不如我国的梵宇那样重视朝向问题,泰国、老挝等地的梵宇朝向常常依据详细的地形地形以及交通条件做调整。正对着梵宇进口的一般是梵宇的大殿。清迈梵宇的大殿如北传释教的大雄宝殿相同是首要的礼佛场所。大殿是梵宇的规范装备,往往占有梵宇的中心方位。清迈梵宇大殿大都是木结构建筑,而泰国中部区域则盛行砖石结构。
左为清迈罗摩利寺大殿,作者摄于2023年1月12日;右为曼谷玉梵宇,作者摄于2022年12月11日与横向布局的北传梵宇大殿不同,南传释教梵宇的大殿一般呈纵向,鸿慈永祜称为“纵深大于面阔”。由于南传释教只供奉释迦牟尼,所以清迈的梵宇大殿中一般都只要一尊佛像,即释迦牟尼佛。有时一尊主佛像的神台之前也会供奉一些小的佛像,但也都是释迦牟尼佛。一般大殿内供奉的佛像与后墙之间有过道可以通行,这个与释教绕行礼佛(顺时针)的崇拜方法有关,佛像后边的通道是为了确保大殿盘绕佛像构成一个完好的回廊。这种绕行礼佛的崇拜方法可以追溯到古印度时期。遭到我国的影响,清迈的许多南传梵宇内也会供给签筒,供信众掣签请示神明的定见,泰国人乃至现已将我国的传统签诗(签文)翻译成了泰文和英文。一同,有的清迈梵宇内也会看到观音菩萨等北传释教的神像,但大都在大殿外立龛,不会供奉在大殿中。除了大殿,一些梵宇也会有戒堂(Ubosot)。与服务信众参拜的大殿不同,戒堂一般是僧伽举办内部典礼的场所,如剃度、授僧职等。戒堂相对大殿规划一般略小。戒堂最显着的标志是外围建立的法轮石(Bai Sema)界标,用以提示该处建筑的崇高性。这种界标是大殿和其他建筑所没有的。
大殿的正后方一般是佛塔。清迈的佛塔类型多样,表现了不同艺术风格的影响,其间以方形城堡式塔和圆形铃铛式塔两种最有代表性,或许都是遭到了缅甸蒲甘佛塔的影响。方形城堡式塔的代表有清曼寺(Wat Chiang Man)、柴尤寺(Wat Jet Yot,意为“七塔刹寺”)和罗摩利寺(Wat Lok Moli,意为“至尊界寺”)内的佛塔。
从左至右:清曼寺塔,作者摄于2023年1月12日;柴尤寺滴洛腊塔,作者摄于2023年2月1日;罗摩利寺塔,作者摄于2023年1月12日圆形铃铛式佛塔的代表有帕兴寺(Wat Pra Singh,意为“圣狮寺”)、松德寺(Wat Suan Dok,意为“花园寺”)和素贴寺(Wat Phra That Doi Suthep,意为“素贴山之寺”)内的佛塔。
从左至右:帕兴寺塔,作者摄于2023年2月11日;松德寺塔,作者摄于2022年5月27日;素贴寺塔,作者摄于2022年5月27日柴尤寺(Wat Jet Yot)的金刚宝座塔则是学习了佛陀释迦牟尼悟道之地菩提伽耶(Buddha-gayā,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城南)的金刚宝座塔。
左为柴尤寺金刚宝座塔,有七个塔刹,故名“七塔刹寺”,作者摄于2023年2月1日;右为菩提伽耶的金刚宝座塔,来源于网络与汉传梵宇比较,清迈梵宇中的藏经阁一般都很小,如帕兴寺的藏经阁(Hor Trai,直译为“三藏阁”)或许压根没有专门的藏经阁。这是由于南传释教严格遵守原始释教的教义,只将最早的一批巴利语释教经典奉为真经(大约公元五世纪定型)。今天泰国奉行的巴利三藏经一套45册,一个大的书橱足矣。而北传释教将许多发生时刻较晚的经典也奉为真经,因而北传释教的佛经卷轶浩繁,比较南传三藏经体量要大许多。因而北传释教寺院中的藏经阁一般也比较大。除此之外,清迈的梵宇也有钟鼓楼相似的建筑。
左为帕兴寺藏经阁,作者摄于2022年11月18日;右为清曼寺藏经阁(补葺中),作者摄于2023年1月12日帕兴寺的戒堂内还能看到一种多层的室内小塔,泰语称为Ku。小塔直达房顶,有如立在室内的柱子一般。这种款式或许和我国西北的中心柱窟相同都起源于古印度的支提窟(Chaitya Hall,或译“塔庙窟”)。
从左至右:古印度支提窟,今印度浦那(Pune),约公元2世纪,来源于网络;莫高窟-254窟,北魏,来源于网络;帕兴寺室内小塔,约建于14世纪,或更晚,作者摄于2023年2月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清迈的梵宇边上常常建有校园,这是由于前史上的梵宇还承当了教育功用。在近代之前,南传释教国家的男性从小都要落发,以小沙弥的身份在寺中学习。传统年代的梵学实践也包含了文学、传统医学乃至建筑学等各种常识,与现在所了解的狭义的、宗教概念上的梵学有所区别。近代之后,校园的功用逐渐从寺庙中剥离,许多梵宇中的沙弥书院开展为新式的校园,因而可以看到许多校园都建在寺庙边上。作为传统,许多新式校园内也会立龛供奉佛像,清迈大校园园内还专门有一座礼佛的法堂。不仅仅是教育功用,传统年代的梵宇也承当了社区活动中心和葬礼服务中心等许多功能。现在有些梵宇内还能看到固定的小吃摊贩以及按摩室。从家庙到国寺:王室与梵宇的联系
清迈的几间重要的寺庙是泰北释教开展史上的“里程碑”,乃至这几间梵宇的前史便是泰北释教史的骨干,而这几间梵宇又都是兰纳王室捐资建筑的。
听说清迈城中东北部的清曼寺是清迈最早的寺庙,由兰纳的开国控制者孟莱王(Mangrai,约1259-1317年在位)建筑。1296年,孟莱王开端建筑清迈城,清曼寺一带是他最早的居住地。可是传世文献中关于孟莱王的记载有许多传说颜色,清曼寺前期前史的记载或许未必事实。依据清曼寺中发现的一方1581年刻成的石碑,该寺在1571年进行了“重修”,也便是说清曼寺或许是建筑于16世纪。
据《庸那迦编年》,1344年,兰纳国孟莱王朝的第4代王坎福(Kham Fu, 1328年-1344年在位)于清盛(今泰国清盛)逝世,王子、后来的第5代王帕育(Phayu,1344年-1367年在位)到清盛火化了坎福,将他的骨灰带回了清迈。为了安放坎福的骨灰,帕育在清迈城中建筑了一座佛塔,在塔四面的龛内建立佛像,然后以佛塔为中心建筑了帕兴寺(Wat Phra Singh)。
这条记载十分重要,或许是兰纳王室实施火葬之始,而火葬是典型的释教殡葬方法。尽管相关史料也记载兰纳国之前的孟莱王、胜仗王(Khun Khrüam,约1317年-1327年在位)都是火葬,但细节都含糊不清,连详细的安葬地都无法查验。到了第3代王盛普(Sæn Phu,约1327-1334年在位)逝世时,相关史料又记载他被以土葬的方法安葬,并完好地记录了安葬地址和随葬品。假如早在孟莱王的年代就现已实施了释教式的火葬,盛普大约率也会被以火葬的方法安葬。由于殡葬方法的挑选并不是一件可以随意更改的小事,况且兰纳国王身份更是显贵,葬礼必定是国中大事。更为合理的解说是,孟莱和胜仗王的年代释教并没有后来幻想得那样盛行,他们或许是以传统的土葬方法下葬的,但由于前史记载的含糊,后世史家也追述他们以火葬的方法下葬,以契合后来释教的教义。而盛普则被史料清晰记载为以土葬的方法安葬,相关的记载就保留了下来。
释教徒以火化的方法处理遗体,这本是很常见的做法,北传释教也是如此,如闻名的少林寺塔林。兰纳国及其他东南亚释教国家的特别在于用佛塔来安放控制者的骨灰。一般来说,佛塔只用于供奉释迦牟尼自己和释教僧侣的遗骨,但东南亚释教国际也开展出了建塔安放国王骨灰的传统。柬埔寨金边的皇宫内也可以看到安放国王骨灰的骨灰塔。这个或许跟他们的王权观念有关。转轮王观念是东南亚释教王权的中心,而南传释教经典《大般涅槃经》中记载有四种人的骨灰可以建塔供奉:如来、辟支佛、如来的声闻弟子和转轮王。大约依据这一准则,南传释教国家构成了建塔安放国王骨灰的传统。
帕兴寺现在现已是清迈城中最为重要的寺庙之一,庙中供奉的佛像Phra Buddha Singh被以为是清迈的维护神,每年的宋干节(泼水节,泰历新年),这尊佛像就会被抬出来巡游,保佑清迈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安居乐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帕兴寺是兰纳的国寺,但就其前史来讲,帕兴寺开端是兰纳王室的家庙,由于其间供奉的是第4代王坎福的骨灰。
到了第6代王格那(Kü Na,约1367年-1388年在位)时期,清迈的南传上座部释教迎来了榜首次大的开展,《庸那迦编年》称为锡兰(斯里兰卡)释教传入清迈之始,首要的标志是松德寺和素贴寺的建筑。在此之前,清迈当地盛行的释教或许是哈里奔猜年代以来的混合了大乘释教和婆罗门教的前期释教。其时素可泰(今泰国素可泰)的和尚拍颂那从马都八(Moke Ta Ma,今缅甸萨尔温江口)学习了完好的南传上座部释教教法和戒律,威望日隆。所以格那派出使团迎请他到兰纳国布道。在素可泰王的允准之下,拍颂那带着一块金黄色的佛骨舍利(听说是古印度的阿育王当年供奉的)来到清迈弘法,许多信众在他的掌管下剃度落发。当人们沫净佛骨时,佛骨放出光辉一分为二。所以格那王命令在清迈城的西门外建筑了松德寺(Wat Suan Dok),用以安顿新出现的佛骨舍利。为了安放原本的那块佛骨,人们把他放到御象背上,请大象来决议建塔的方位。所以大象自行走到了城西更远处的素贴山顶上,停住不动了。格那王和拍颂那便决议在素贴山顶建筑佛塔,将佛骨埋入塔中,这便是素贴寺之始,其时在1386年。至今在松德寺殿内还能看到岩画描绘格那王二分舍利、建筑松德寺和素贴寺的故事。
松德寺岩画,作者摄于2023年2月11日。画面中心下方的两个人物为高僧拍颂那和兰纳王格那,中心上方为松德寺塔,右上方为素贴寺塔。尔后由于南传释教的盛行,兰纳王室以佛塔来安放国王骨灰的殡葬方法变得更为盛行。听说格那王身后他的魂灵不得安眠,所以托梦给自缅甸蒲甘归来的商人,让第7代清迈王昭盛孟麻(Sæn Müang Ma,约1388年-1401年在位)于清迈城中建筑一座大塔。该塔在第9代王滴洛腊(Tilokarāja 约1442年-1487年在位)时被加高至90米,成为家喻户晓的一座大塔,这便是现在清迈市中心的柴迪隆寺(Wat Chedi Luang, 意为“大塔寺”)。尽管相关史料未能言明该塔下埋的是格那的骨灰,但至少可以必定的是这座塔是他的积德行善塔。现在许多人信任这座大塔下便是格那的骨灰。惋惜的是这座塔在16世纪中期由于地震坍毁,现在仍能看到残存的巨大塔基。
左为柴迪隆寺塔,作者摄于2022年11月18日;右为柴迪隆寺塔灯火恢复造型,来源于网络滴洛腊自己身后,其骨灰被承继人葬在城北的柴尤寺大塔内,这座城堡式塔前面至今仍建立着滴洛腊的雕像。清迈郊外西北角的罗摩利寺则是兰纳王室在16世纪的首要宗族墓地,听说缅甸吞并兰纳国后扶持的维素蒂黛维女王(Wisutthithewi,约1564年-1578年在位,终究一位有孟莱血缘的清迈控制者)身后便是葬在该寺的一座塔内。这几座寺庙是清迈规划最大、位置最重要的几座寺庙,而这几间寺庙都和兰纳王室有十分接近的联系,乃至原本便是兰纳王室的家庙。正是在兰纳王室的大力提倡之下,清迈等地的释教才得以开展壮大。时至今天,这种王室和寺庙的接近联系仍能从一场清迈旧贵族的葬礼中观察到。
公主的葬礼:从帕兴寺到松德寺2023年的2月11日,泰国清迈市的民众为贵族女人昭庄德(泰语名字为Chao Duang Duean Na Chiang Mai,汉语名字为作者音译)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宛如节庆时的嘉年华巡游。清迈这场葬礼的特别性在于逝者的贵族身份以及葬礼中浓郁的释教要素。夸大地说,这场葬礼简直是“活着的前史”。
昭庄德生于1929年的5月22日,其时正是南传释教的卫塞节(泰历六月的月圆之日,南传释教以为释迦牟尼出世、成道和涅槃都是在这一天)。因而她得名Duang Duean,意为“命中注定的(吉利)月份”。Chao是对贵族的敬称,常冠于名字之前,约略等于尊下。Na Chiang Mai 是她的姓。泰国(暹罗)人本没有姓氏,拉玛六世(Vajiravudh,1910年-1925年在位)在1912年要求暹罗人要申报自己的姓氏,从此今后暹罗人才开端有姓。控制北部清迈的王族(七兄弟王朝)被拉玛六世赐姓Na Chiang Mai(意为“在清迈”)。
昭庄德女士自身其实是清迈七兄弟王朝的远支王族,并不是真实的公主。兰纳国七兄弟王朝的榜首代王卡维拉(Kawila,1782年-1816年在位)在暹罗的支撑下驱赶了占有兰纳国的缅人,创始了被称为七兄弟王朝的兰纳国新时期。昭庄德的祖上是兰纳七兄弟王朝的第3代王披耶坎番(Phraya Khamfan,1823年-1825年在位,卡维拉的弟弟),但昭庄德的父亲仅仅南奔的一个小领主。昭庄德出世今后被第9代清迈王考纳瓦拉特(Kaew Nawarat,1910年-1939年在位)的女儿Chao Bua Thip Na Chiang Mai公主收为养女,并接受了比较好的宫殿教育。因而昭庄德后来被赐姓Na Chiang Mai。老太太生前做过清迈市政委员会的委员以及泰国的国会议员,还做过清迈一家报社的司理,以及北部报业联合会的副会长以及电台掌管人。除此之外,老太太还做过许多慈善事业,2015年被评为泰国的“年度白叟”。由于她的贵族血缘和社会影响力,人们也称她为公主。
兰纳七兄弟王朝自榜首代王卡维拉开端一向向南边的暹罗纳贡,一同也保留了很大的自主权。19世纪后期,英国和法国也纷繁向中南半岛拓宽实力。依据James Ansil Ramsay的研讨,由于兰纳国丰厚的柚木资源,许多英国商人来到清迈等地从事木材交易,奉行自由交易的英国商人对清迈的各级领主索要规费等行为越发不满。早在1855年英国就和暹罗签定了推广交易自由化的不平等公约《宝宁公约》(Bowring Treaty),所以英国人就期望暹罗政府可以依据《宝灵公约》出头处理兰纳境内的交易胶葛,维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这就面临着《宝灵公约》是否适用于兰纳的问题。所以就有了前后两次《清迈公约》,将暹罗对兰纳的控制清晰化。1874年,榜首次《清迈公约》签定今后,暹罗官员有史以来榜首次进入了兰纳区域,首要为了处理缅甸边境的伏莽问题以及木材交易胶葛。1883年第2次《清迈公约》签定今后,暹罗派来的参谋开端直接接收清迈王和高档贵族们的权利。1896年,暹罗在曼谷成立了森林局,完全掠夺了兰纳国的当地贵族出卖柚木的权利。1902年,暹罗在清迈设Phayap省,兰纳终究就被暹罗完全吞并。从第7代清迈王英塔腊威柴亚暖(Inthawichayanon,约1873-1896年在位)开端,兰纳国贵族们的权利就越来越小。第9代清迈王考纳瓦拉特现已没有了实践的政治权利,他的首要工作是一名军官。1939年,考纳瓦拉特逝世,清迈王的尊号被正式废弃。
时至今天,清迈的旧王族们早已没有了旧日的荣光。清迈王血缘的承继人昭翁萨格那清迈(Chao Wongsak na Chiangmai,1935年生,考纳瓦拉特的孙子)现在仅仅一个航空工程师。这些贵族在典礼上仍享有必定的尊荣,如掌管对兰纳先王的纪念活动等。一同,如本文的主人公相同,清迈、帕府和难府等兰纳旧地的高档贵族逝世今后也都会依照传统举办贵族式的奢华葬礼。跟着时刻的消逝,这些衰败贵族的奢华葬礼或许就不会再举办,就像他们的先人从前失掉权利相同。清迈友人说我真的是很走运,他们也没见过这样的阵仗,并且今后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
昭庄德在2023年的1月2日逝世,通过长时刻的预备,她的葬礼在2月5日开端举办。前几日的活动首要是在停灵的帕兴寺举办诵经典礼和施舍典礼。所谓施舍便是向和尚供养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2月11日是整个葬礼的终究一天,逝者的遗体将被从帕兴寺拉到城西的松德寺火化。终究的火化环节中,远在素贴山顶的素贴寺也派出了大方丈参加,可以说这三所最重要的寺庙都参加了昭庄德的葬礼。如上文所说,帕兴寺、松德寺和素贴寺与前史上的兰纳王室有接近的联系。卡维拉克复清迈今后也活跃资助梵宇的兴建和补葺,如柴迪隆寺。现在看到的清迈古庙其实都很难说完全是开端的样貌,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七兄弟王朝以来的补葺或改造。
00:51
昭庄德女士的葬礼可谓“活着的前史”。(00:50)下午二时许,盛装的游行部队(送葬部队)开端动身。部队的先导便是一位高坐在车架上的和尚。除了参加巡游的各界大众,整个部队的中心是90名小沙弥和10名大和尚牵引的灵车。在释教的观念中,僧侣是佛陀教法的传承人,是佛、法、僧三宝之一,位置爱崇。一般来说,僧侣和佛像相同都是释教徒顶礼膜拜的目标,可是在这位清迈贵族的葬礼中,和尚却亲身牵引逝者的灵车行进。北传释教净土宗有接引佛的观念,说是接引佛和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一同引导逝者往生西方净土。某种程度上说,昭庄德的葬礼上牵引灵车的僧侣是实实在在的接引佛,他们将扶引逝者升入极乐国际。依照我国人的观念,牵引灵车的人一般都是逝者的亲属或许联系接近之人。从这个视点来讲,牵引灵车的这些僧侣也是清迈王室和僧侣集团联系接近、相互扶持的一个明证。两个集体可以说是深度交融在了一同。
从左至右:游行的部队;牵引灵车的僧侣;游行部队中的大象。作者摄于2023年2月11日在终究火化典礼进行前,还举办了一个施舍僧衣的典礼。宾客们纷繁上台,将预备好的僧衣放到火化亭的基座上。然后一群小沙弥再上台,排队取走宾客们刚刚放在火化亭上的僧衣。这样,这座火化亭实践上也成了传递积德行善的一个渠道。这也是清迈控制者支撑释教的一个比如。大约到了晚上七点半,火化典礼开端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火化亭是用焰火来点着的。先是有一个如小火箭的炮仗拖着哨声盘绕了火化亭一圈,终究撞击到火化亭上,点着了火化亭四周的焰火树,宣布五颜六色的点点星光;再之后是火化亭顶上如水银泻地一般流下的焰火瀑布;终究是火化亭底座开端宣布绿色的烟雾,伴跟着如大象呼啸一般的呜呜声。火化亭就在这模仿大象的悲鸣声中被点着了。伴跟着“焰火秀”的是周围观众的阵阵惊叹,整场葬礼庄严但并不沉重。终究到晚上八点半火化亭连同逝者的棺木一同燃尽,人们才终究散去。
整个火化的进程有一对消防员在旁边驻扎。同行的泰国人告诉我,他们的使命首要是避免火势失控,由于火不能从火化亭的基座上燃起,只能从顶上燃起,以避免亭子提早坍毁。一同,消防员也不断地向空中浇水制作水幕,以净化烟尘,避免火星飞到别处引发火灾。传统的释教葬礼和现代的消防技能就这样调和地出现在同一画面中。
从左至右:焚烧前的火化亭;焰火下的火化亭;燃尽的火化亭。作者摄于2023年2月11日从空间布局和艺术风格上看,清迈的梵宇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是泰人文明与古印度、斯里兰卡、缅甸和柬埔寨文明的交融与再造。从时刻尺度上看,清迈的梵宇是兰纳的王室与僧侣集团相互扶持、同享权利的产品。昭庄德女士的葬礼则以一种最鲜活的方法将清迈梵宇的前史与实际、空间与时刻勾连了起来。(本文来自汹涌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汹涌新闻”APP)
告发/反应
相关文章
莆田8岁男童在野山迷路三天,救援力气将对山上4个地址要点搜救
新京报讯(记者彭镜陶 实习生郑雅璇)5月4日下午,福建莆田仙游县石谷解,一名8岁邹姓男童跟从家人爬山时不小心迷路。5月7日上午,新京报记者从莆田市曙光救援中心得悉,现在孩子仍未找到,其时山中仍有大雾。...
身高1.8米!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半马冠军是它
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4月19日一早,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参赛主体的半程马拉松赛事——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正式开跑。封面新闻记者从主办方得悉,此次参赛的人形机器人部队共20支,优必选科技、乐聚机...
吃瓜网吃瓜网友科普:道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探索自然与和谐的哲学
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许多人都在追求心灵的宁静和生活的和谐。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自然观和人生态度成为了人们探索内心世界的有力工具。那么,道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在...
在密西西比州的桑德希尔镇,托丽像野鹿相同奔驰跳动,运动是她的独爱。
美国奥运冠军在家临产逝世,尸身10天才被发现?!美国网友:离谱但常见
在密西西比州,托丽·鲍伊(Tori Bowie)是被光环笼罩的体育名人。她出生于1990年,几个月大时被母亲扔掉,祖母经过寄养组织取回了监护权,将她抚育长大。在密西西比州的桑德希尔镇,托丽像野鹿相同奔...
51朝阳吃瓜群众网2025年6月12日
连日来,河南多地持续高温出现不同程度旱情,引发关注。目前河南情况如何?当地采取了哪些抗旱措施?国家对抗旱又有何举措?一文速览。 “台湾民意基金...
166.su网友科普:存心的近义词是什么?深度解析
166.su网友科普:存心的近义词是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需要表达"存心"的意思,但如何用更丰富的词汇准确传达这种意图呢?166.su网友通过深度解析,为大家整理了以下近义词,帮助提升语言表达的...